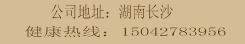![]() 当前位置: 马里 > 旅游景点 > 去了一趟马来西亚旅游,半条命差点都没了
当前位置: 马里 > 旅游景点 > 去了一趟马来西亚旅游,半条命差点都没了

![]() 当前位置: 马里 > 旅游景点 > 去了一趟马来西亚旅游,半条命差点都没了
当前位置: 马里 > 旅游景点 > 去了一趟马来西亚旅游,半条命差点都没了
点击上方的“施施小洛”可以订阅我哟~
“小洛·惊奇勿语”系列第24个故事
对不住你们,拖了三期!
对不住!!!
PS.文末扫码进群哟~
前文回顾
《不要随便去会所酒吧夜店,否则,你都不知道你会不会变成饲料》
《不要在大雾天开车,否则,遭遇车祸都算是最轻的后果,你还可能会…》
《95后真·女道士深夜与闺蜜男友独处一室!怎么办?在线等!挺急的!》
这一觉睡得格外沉,仿佛很久没有不做噩梦地这样睡一大觉了。梦里那个少年一直对我笑,他说,你好啊,好久没见,看你过得实在不怎么样,我只好回来了。
醒来的时候,我还躺在宁姨家客厅的那张宽大的沙发上,一睁开眼,就看到了我的行李箱——24寸,柠檬黄,贴满了各种花里胡哨的贴纸,确实是我的没错。
大概三分钟后,我才从沉甸甸的梦境里清醒过来,又过了半分钟,才终于回想起来昨天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可是,我的行李箱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刚从沙发上坐起身,一个绑着高马尾的少女就坐在了我身边,问我:“看来睡得还不错?”
我又反应了十秒钟才想起来,这是少女道士莫清缘。她今天换了一件浅蓝色的粗毛线毛衣,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把眼前这个少女和昨晚那个“驱邪”的女道士联系在一起。
啊,世界真是奇妙。
她见我盯着自己的行李箱发呆,了然地说:“雪鸟连夜回去给你收拾的行李,你再休息一会儿吧,待会儿就出发去机场了。今天飞沙巴。”
我:???
少女道士见我脸色不好,补充了一句:“美人鱼是你们那个社区的管理员,有你房间的门卡,也是她进屋帮你收拾东西的。雪鸟说给你发过消息报备了,可你睡得太沉,八成没有看见。情况紧急,你也别太在意了!”
我摸到塞在身下的手机,打开来看,果然有几条美人鱼发来的消息,叹了口气。想了想,我问:“签证还没办,怎么去马来?”
媛媛笑起来:“有钱人的世界,你我都不可能清楚看懂的。”
哦,意思就是,宁姨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咯。好的,霸道总裁本裁了。可惜是个女的。
这时保姆端上了早餐,我才感觉到肚子咕咕叫,仿佛昨晚那场梦耗掉了我身体里仅存的一点力量,导致我醒来这么久,还是心不在焉,魂不守舍。
我俩吃了早餐,我才想起来问雪鸟到哪里去了。
媛媛耸耸肩:“和宁姨、六叔提早过去安排了。”
“怎么你没去?”
“暂时用不上我。我留下来跟你一块儿去。”
“为什么非得带上我?”这句话问出口,面前的少女沉默了,可是我坚信她知道些什么,那些雪鸟和随风都没有告诉我的,更多的真相。
不然为什么呢?如果真如随风所说,是为了给我解决官鬼压身的大劫,或者如雪鸟所说,我就是一个活体吉祥物,可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我其实没有任何作用啊,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参与者,甚至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累赘。就像这次去马来的案子,这么大的案子,背后的风险可想而知,所以雪鸟才会临时喊上这个女道士,那为什么又要多费周折地带上我呢?
这背后一定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这或许才是真相。
媛媛沉默了许久,一直到保姆过来提醒我们准备出发,司机刘岩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我已经放弃从她口中得到只言片语了,她才突然开口:“他们确实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理由,不全是为了帮你,你可以理解成互相利用,大可不必自责。”
她起身拿起自己的维尼熊背包,“反正,对你来说,只有好处,也不会失去更多了。”
飞机在哥打京那巴鲁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已经是傍晚时分了。我有些遗憾宁姨没有为我们准备商务舱的座位,却又暗自有些庆幸。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虽然贪财好色好吃懒做,但无功不受禄,无法给予回报就不敢奢求得到,否则心有不安,吃不下睡不着。
所以我必须弄清楚,莫清缘说的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才肯跟她一起,由司机刘岩陪同,飞到了马来西亚。
机场停车场已经有车等着了。令我意外的是,刘岩直接坐到了驾驶座上,然后轻车熟路地开上了路,甚至没有导航。
刘岩不是上海人吗?或许因为他是孟贺林的司机,所以常来马来,对这里轻车熟路吧。这个疑问只在我的脑海中冒了个头,我就又陷入了沉思。
旁边的莫清缘换了吊带和热裤,目测腿比我的长了三公分,我忍不住盯着看了很久,终于没忍住,问她:“当代女道士都是你这样的吗?”
她摇摇头:“这是你们对宗教的误解和偏见。”她摇下窗户,热带的热空气钻了进来,“应该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应该’是谁定的?”
想起这些年身边的朋友遭遇过的各种评价。
“你看上去一点也不像结婚了。”
“你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当妈妈了。”
这个“像”的标准,又是谁定义的呢?
我忽然觉得她很酷。
而我,一点也不酷。
又发了一会儿呆,我问司机刘岩:“我们现在是去闫氏集团吗?”
刘岩回答:“根据宁总给我的酒店地址,那里并不属于闫氏集团。雪鸟老师已经提前抵达了。谈判时间定在明天。”
媛媛转过头来看向我,说:“这是我和雪鸟昨晚定下的对策。换一个谈判地点,布置好一切该布置的,来一个请君入瓮。”
酒店位于沙巴海岸。
车在酒店门口停下,就有门童来搬行李,有服务生直接引我们进房间。入住手续也省了,看来早有人打点好了一切。
也来不及休息,媛媛就要去忙了,对我说:“海滩就在后面,你可以去痛快玩一场,所有消费记账,会有人给你结账的。没准还能撩到个帅哥。不要浪费机会哟,明天可能是一场硬仗。”
我哪里有心情去沙滩海浪比基尼啊,媛媛拗不过我,还是答应带着我一起去找雪鸟,但还是数落我:“你说你啊,老老实实享受不就好了吗,非拼着要给回报,我该说你什么好……”
被一个二十岁的大学生数落,我有点不太开心,却又无法反驳。
雪鸟这会儿正在明天谈判要用的会议室里。我们过去的时候,他已经将会议室布置得差不多了,在做最后的调整。
见我们到了,他寒暄两句,便接着去忙了。我实在很好奇这些风水上的东西,四处转转。
这是一个标准的五星级酒店会议套间,外面是休息室,里面是会议室。
休息室里摆放的是中国古典木椅和八仙桌,我猜这应该出自雪鸟的手笔,因为以这个酒店的装修风格,原本的配置应该是皮沙发和玻璃金属茶几。
会议室门口摆放了两个木制折叠屏风。屏风的后面贴了两张用朱砂绘制的门神,看起来是雪鸟亲手画的。会议室的后面还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屏风,正好遮挡住了一尊道主画像。
雪鸟和媛媛说了需求,媛媛从背包里拿出了道具,挥手画了好几张符——一个穿着吊带热裤的高马尾长腿美少女画符,这画面真的一点也不违和,真的!——雪鸟再将这些隐蔽地贴在了会议室的窗口各处。
会议室里面的桌椅子的摆放,雪鸟也做了相应的调整。把长桌换成了大圆桌,并按照八卦方位,把入席的人的名签摆好,又在圆桌中间的位置,摆放了一株桃树盆摘。
我以为这样就差不多了,雪鸟又进了会议室的洗手间,在镜子对面挂了一张钟馗画像。
他俩一阵忙活,我在一旁完全看不明白。一个好好的高级时尚简约酒店,莫名其妙就成了中国风——还是老式的,我的审美实在有点跟不上。
这还不算完,雪鸟说:“去你们的房间。”见我一脸不理解,耸耸肩,看向媛媛,“这要教,可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说了她也不明白。你要乐意解释,你就给她解释好了。”
莫清缘一脸黑线。
接下来雪鸟又对我们每个人的房间进行了一番布置,重点当然是宁姨的房间——他竟然从上海带来了大量宁姨的私人物品,在这间宽敞的套房里,摆放了宁姨常看的书、茶杯、酒具,衣柜里摆满了宁姨的衣物,甚至给床铺换上了全套床单被褥……
雪鸟是懒得给我解释了,媛媛倒是挺好心,告诉我这叫反客为主的风水局,“这些物品的选择和摆放看似随意,但其实用地支隐藏天干,暗合了宁姨的八字。简单来说,这里虽是客场,但反客为主,住在这里相当于在自己家中了。”
一切准备就绪,大家各自回屋休整。夜里,大家都睡不着,雪鸟喊我和媛媛去海边吹海风。大家坐在沙滩上,听着海浪声,喝着冰啤酒,竟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如果只是来度假的该多好。如果背后没有那些沉甸甸的疑问该多好。如果,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编辑该多好。人为什么要预知自己的未来呢,什么都不知道,懵懂地过完这或长或短的一生,劫难来了也便来了,死了也就死了。提前知道,却无能为力,有什么益处呢?
媛媛突然举起酒瓶和我碰了一下,盯着海的远处,说:“我四岁入道观,属于普通人的三观还没来得及建立,就知道了这个世界其实和大多数人以为的不太一样。但我得融入这个世界,融入大多数人,所以,我必须看起来是一个‘正常’的少女,普通的学生,一个‘不太像女道士的女道士’。”
她又向雪鸟举瓶,雪鸟和她碰了一下,一口干了。
她接着说:“雪鸟和随风也是一样。我们都是生来即在世界的另外一个维度里。”她看向我,“但是你不一样。他们两个直男,可能不能理解你那些细腻的情绪,但我懂。尤其是我在面对普通世界的人际关系感情纠葛时,我也曾经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学生。”
我叹了口气,没有答话。
她笑起来:“洛姐,你原本就不是普通人,但你一直在普通人的世界里,你应该为此庆幸,这是你的幸运。如今运气用完了,你需得面对真相,你已经跨进来了,就再回不去了。这里面的平衡,你只能自己把握。”
二十岁的少女,竟然在安慰我。这也是我从被雪鸟带进另一个世界以后,第一次有人和我讨论这些情绪。
我一时无言。
雪鸟没再接着喝酒,而是说:“小洛,有的事,如果你一定想知道,总会知道的。”
我条件反射地想要怼他一句,他却转移了话题:“这次的事情过了,先想办法把你身上的降头解了。”
降头???我一脑袋问题,是我知道的,电影里演的那种东西吗?
我什么时候中过降头?
雪鸟刚准备回话,他的手机响了,是宁姨打来的电话。她说,自己住过那么多酒店,从没有这次这样感觉舒服。雪鸟又嘱咐了宁姨明天的注意事项,这才挂了电话。
这么一打岔,谈兴都弱了。雪鸟看看时间,已经很晚了,便让我们都回去休息。
我知道再问什么也问不出来,只能憋着一肚子疑问回了房间。
唉,又一个不眠之夜了。
谈判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九点。
这个时间点,是闫昆强烈要求的,谈判地点听了宁姨安排,谈判时间只好做了让步。
昨晚整晚没睡着,于是这个白天我几乎在酒店房间里倒头睡了一天,傍晚饿醒过来去吃饭,才知道雪鸟和媛媛出海潜水去了,也没叫我,令我懊恼万分。
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还有兴致出海,心也真是够大的!
晚饭后,我们在酒店大堂和宁姨碰头的时候,她穿着白色西服套装,十分干练。跟在她身边的六叔穿着黑色的西装,两人一白一黑,倒是挺搭。
如此着装是雪鸟的要求,因为宁姨的日主天干为水,金生水,白衣正好能旺她。雪鸟还送了宁姨一串白水晶手串,让她戴在左手上。六叔的日主天干为金,黑色代表水,水生金,在命理上是宁姨的辅助。
会议室里已经备好了顶级乌龙茶,这是待客的饮品,雪鸟已经嘱咐过我们,在谈判桌上尽量少喝茶。至于为什么,天知道,反正我不知道。
九点,双方准时进入休息室。
闫昆随行一共五人,果然还是带着那个会“控鬼术”的唐装男,其余几人便没见过了。这唐装男的脸色有些苍白,看向雪鸟时,眼中竟然有些说不清的复杂神色,不复上次见面的那种阴鸷。
闫昆一行五人刚坐下,雪鸟就立刻招呼服务员上茶。冒充服务员的媛媛悄悄白了他一眼,又冲我吐吐舌头。
也亏得雪鸟想出这么个歪主意。
我注意到室内的温度有点低,应该是特意提前把空调打开,并且将温度调得很低。
闫昆等人便喝着热茶,吃点点心,休憩片刻,双方假惺惺客套了一下,然后一起进入了会议室。
我看到唐装男——其实他今天并没有穿唐装,而是身着一件遍布古怪刺绣的黑色西装,至于绣的什么图案,我就看不懂了,但总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的手里拎着一串暗红色的手链,小手指上还挂着一串小金铃。
双方在会议室里就坐,雪鸟使个眼色,媛媛又送上了热茶。
唐装男从包里拿出了一个小香炉,在闫昆的右手边点燃两柱香。闫昆笑呵呵对宁姨解释说:“哈哈,最近休息不好,点几支香,提神。”
我这个外行都能听出来,这句话是骗鬼的。一般人在家中焚檀香,只点一支香,或者三支香,一支香寓意平安,三支香为三宝,都没什么大问题,两支香代表什么?阴阳两界,多是用来沟通阴灵的。有没有阴灵另说,但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雪鸟没吭声,由着唐装男作为。
唐装男点燃香,又取出一只空茶杯,倒好茶,摆在香炉旁边,然后站在闫昆的身后,双手拢在袖子里,神情冷漠。
雪鸟见他都摆弄完了,这才挥挥手。
我和媛媛对视一眼,起身行动起来。我们先关上会议室的门,然后拉开门口的两扇屏风,挡住大门。如此一来,屏风后的两尊门神显露了出来。
我察觉到唐装男神色微微一变,但他没多说什么。
我和媛媛又走到会议室后面,拉开那两扇屏风。那尊道祖雕像显露出来的时候,唐装男的脸色立刻大变,脸色愈加苍白。
霎时间,房间里好像卷起了一阵阴风。唐装男急忙走到闫昆跟前,将香炉里的香折断,并且一口喝掉碗里的水,面色铁青地往洗手间走去。
可当他打开洗手间的门,看到里面镜子里映出的钟馗像的那一刻,面色陡然变得铁青,紧跟着一口血吐了出来,整个人萎靡地倒在了地上。
闫昆惊讶地站了起来。在场的宁姨、六叔也都大吃一惊,我一时间也有些不知所措。
这和雪鸟交代过的不太一样啊。他说如果成功的话,唐装男只会身体不适,症状犹如缺氧,嘴唇发白头晕目眩,没说会吐血倒地这么严重啊!
我见媛媛脸上也有意料之外的吃惊神色,雪鸟都有些懵,便知道,事情确实超出了他的计划。
好在雪鸟很快反应过来,叫来早就在一边候着的医生,把唐装男抬去休息室休息。然后,他拿出备好的几块玉石球,放在了会议室东北角的一个架子上。
唐装男的意外,让闫昆一时有些狼狈。但他依旧镇定自若,在谈判桌上胡搅蛮缠,示图将水搅乱,终止这次谈判。
但宁姨却很有耐心,不急不躁,和闫昆磨洋工。
谈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后,宁姨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六叔看了下号码,把手机递给了宁姨。宁姨听完电话后,脸上终于露出了微笑。
随后,她的气势陡然一变,从六叔手中拿过几份文件,甩在了闫昆面前,说出了闫氏集团目前面临的各种困境,和宁姨早就已经暗中操作过的一些手段。
这才是真正的商战片的剧本嘛,这场大戏总算从霸道总裁玛丽苏到东南亚恐怖B级片的邪路上绕了回来。
剧情进行到这里,和闫昆一起来的闫氏集团的几个董事已经有些坐不住了,我们都以为宁姨稳操胜券的时候,窗外忽然又响起了一阵铃声。
“叮铃——”
“叮铃——”
“叮铃——”
和前夜在宁姨家听到的,一模一样。
唐装男吐血昏迷,还在隔壁躺着,这铃声又是从何而来?!我们几人面面相觑,闫昆却一副“你们等着瞧”的得意神色。
我往窗外看去,果然,夜色之中,雾气渐浓。可是前夜这铃声刚输过一仗,这次又故技重施,能起什么作用呢?
我还在困惑,媛媛已经迅速到窗前检查她之前贴好的符纸,确认没问题后,对雪鸟点一点头,闪身出去了。
雪鸟叹口气,对宁姨和六叔说:“你们先别离开房间,关好门窗。”又有些担忧地看看闫昆,“闫总,麻烦你也先留在这里不要离开。”
闫昆原本就没有要离开的打算,其实大家都知道,这背后捣鬼的肯定是他,却又无可奈何。
我等着雪鸟给我分配个什么任务,他盯着我看了半晌,才说:“小洛,你去隔壁看看那位先生。”他看向闫昆,“那位先生怎么称呼?”
“冯。”闫昆只答了一个姓。
雪鸟对我说:“你去看看冯先生有无大碍。万一有事,你请酒店工作医院。”我顿时明白了他话外的意思,说是让我去看看,其实想让我去确认。
或许因为我双官双印,对方的手段对我不会起什么作用,这才放心让我去吧?
不管怎样,能帮上忙,总是好的。
我和雪鸟一同离开了会议室,他往酒店大堂而去,我拐到会议室右侧的一间客房里,推门进去,却并未见到那位冯先生。
我心中有不祥的预感,出来找到一位服务员,有蹩脚的英语和他沟通半天,他才明白我的意思,指指外面,意思那位先生刚才出去了。
吐血昏迷,这么快就恢复了?
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我转头就往外疾步走去。要赶紧找到他,虽然我不知道我找到了他我能做什么,但必须找到他。
“叮铃——叮铃——”
“叮铃——叮铃——”
“叮铃——叮铃——”
铃声又响了起来,这是第二遍了,节奏更快更急了一些。我感觉到大脑开始有些混乱起来,联想到两天前的那一晚,心里暗暗分析,虽不知道这铃声到底有什么古怪,但想必是诱发了我中的什么降头吧?
降头到底是什么鬼东西?我为什么会相信这种鬼东西?!
我得找到那个姓冯的,必须找到他。这个念头支撑着我,但还不够,我抬起左手,掌心里的那道伤痕还没有痊愈,我狠了狠心,用指尖狠狠地扣了上去。
一阵剧烈的疼痛,让我的大脑清醒了不少。
在铃声响到第三遍之前,我必须找到他!
酒店大楼外,是一大片绿地花园小树林,浓雾弥漫,竟有不少游客坐在花园里研究这在热带地区实在少见的迷雾。没有人感到害怕,也没有人受到铃声的影响,仿佛他们根本没有听到。
我不懂用符文定位,更不会做纸折的符船,身上也没有罗盘——有我也不会用,根本不知道应该去什么方向找,只能凭借直觉。
反正人生地不熟,走到哪里算哪里吧。能见度这么低,前面三五米处有什么都看不清,认不认识路似乎也不是很重要。
待我意识到的时候,发觉自己走到了酒店的停车场里。这是一栋半开放式的建筑,五层楼高,每一层楼的走道上都种满了热带绿植,宽大的枝叶从楼上垂下来,让这栋建筑仿佛一座森林。
这时,我听到了第三次铃响。
“叮铃——叮铃——叮铃——”
“叮铃——叮铃——叮铃——”
“叮铃——叮铃——叮铃——”
脑子被什么堵住了一样,无法再思考问题了,我下意识地举起左手就要去抓掌心的伤口,可是手却沉重得举不起来。
就做一个普通人不好吗?就老老实实地朝九晚五不好吗?就认认真真过好每一天等着那个别人口中的劫难到来不好吗?就,乖乖等死不好吗?
这样想着,我的左手摸到了裤子口袋里的一个硬物,拿出来,竟然是一把匕首。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在口袋里揣进一把匕首的。
我把匕首拿在手里,看了一会儿,就要往左手手心扎下去。反正,总是要死的,还不如赶紧死了,也省得拖累别人。
眼前的一切仿佛被谁点了慢镜头。我眼见着那刀尖就要扎到皮肤上,要刺进去了,哪有最后那一点点距离的时候,又一声铃声响了起来。
“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叮铃叮铃——”
我顿时清醒过来,看到已经扎到手心的匕首,吓得一抖,赶紧把匕首扔了出去。
这一声铃声,和刚才听到的完全不一样,节奏不同,音质不同,应该发自不同的器具,应该是完全不同的人发出来的。
是雪鸟吗?还是媛媛?
这铃声毫无敌意,似乎是它唤醒了我,救了我。我放下心来,顺着这声音找了过去。
不太远,就在停车场的四楼东边拐角处,我找到了铃声的来源。
那是一个头戴暗色藤制斗笠、手里拿着一根锡杖的人,他在不断地摇晃着那根锡杖,随着他的摇晃,锡杖顶端的圆环互相碰撞,隐隐约约有“叮铃、叮铃”的声音传来,就是这声音,刚刚救了我。
我走近那人,他对我的到来似乎有些意外,但又似乎顾不上躲开。
我走近他,微微探身,看清了他藏在斗笠下的脸。
竟然是那个姓冯的唐装男人。
我在冯先生身边坐下,没有说话,也没有打扰他。雪鸟交给我的任务,是看好这个神秘的人,我做到了。何况,直觉告诉我,他是在帮我们,虽然我没有搞明白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阴谋斗争,但他的锡杖发出的声音,能帮助我保持清醒。
他一直在专心默念着什么,锡杖随着他的抖动,不时发出声响。远处那可怕的铃声越来越急,他的锡杖也越来越急,仿佛这两股力量正在较劲,要争一个胜负。
也不知道媛媛和雪鸟在做什么,是不是也和前夜一样,在想办法对付那铃声。
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清醒,这样看来,前晚那人并不是冯先生,那么,害死孟贺林的也不是他了?也许,雪鸟和媛媛成功了,真相就能大白了。
我正发着呆胡思乱想,远处的铃声陡然一停,近处的锡杖也随之停了下来。冯先生看向我,有些意外地问:“你,双官双印?”
怎么谁都能知道?!说好的大秘密呢?!
我刚想回话,就意识到自己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就像刚刚跑完十公里又游了几千米一样,全身虚脱,再说不出话来。
不管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此刻清清楚楚地知道了,我的身体确实出了什么问题。
冯先生见状,也不再问什么,在我身边坐下,抓过我的手腕把脉。
会控鬼,会摇锡杖(鬼知道这是什么招数),居然还会把脉?算了,反正他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我也不吃亏,也没有力气反抗,便由着他去了。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没有说话。这时雪鸟和媛媛也赶了过来,雪鸟看到我还活着还在喘气,仿佛送了一口气。媛媛竟然上前给冯先生行了个礼,诚恳地说:“多谢先生。”
看到雪鸟来了,我的精神一松,左手掌心的伤口剧烈地疼痛起来。然后,我就晕了过去。
晕过去之前,我的最后一个念头是,靠,我怎么这么没用!
一直到返回上海,我都再没见过冯先生。雪鸟和媛媛一切正常,宁姨跟六叔也丝毫没有受到影响,闫昆在这次谈判中全面败退,这一仗,宁姨赢得漂漂亮亮。
故事的真相其实颇有些意思,那令我神志不清的铃声,是一种铃音蛊,令我们都万万没想到的是,背后下蛊的人,竟然是一直深得宁姨信任的司机刘岩。至于刘岩是半途受到谁的收买,还是从一开始就是被精心安插进来的棋子,就不是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够管的事情了。
孟贺林的仇会不会算在他的身上呢?我也不知道。
冯先生早年受过孟贺林的恩惠,这次倒确确实实是想帮忙。吐血晕倒都是他假装的,雪鸟那点布置还不至于令他受创到那个程度。这人的来历十分神秘,既会养小鬼,还养古曼童,看来亦正亦邪。对整件事也不多作解释,事情完结后就不告而别了。
只有我,身体莫名变得非常虚弱,回到上海以后,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却什么都没有查出来。我身体一向很好,这无来由的虚弱,令雪鸟也很有些手足无措。
随风回上海以后,他俩聚在一起研究了一通,得出了一个神奇的结论——
我身上的降头,怕是在一年多前被雪鸟拖去工厂解风水局(点击查看故事《被悬疑作家拖去解风水局的诡异往事》)的时候,就被中下了。只是我体质特殊,命格又硬,一直没有诱发出来,因此被他们忽视了。
说到这间往事我就来气,这事儿似乎不好解决,后续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可雪鸟从没给过我一个真正的解答。
几年以来,仿佛我身上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反而麻烦渐多,疑问更多。他们不愿给我明确的答案,总是模棱两可不清不楚。
如今这降头的问题不能善了,我能不能活到大劫来的那天还难说呢。
宁姨最后封了一个大大大红包,雪鸟给了我三分之一,也足够我把武汉的房贷全部还掉了,聊以安慰。
可是,看着他拍着胸脯保证,一定想办法尽快给我解降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只有冯先生最后和我说的那句话——
“不管是谁在带你解决官鬼束缚,想保命的话,离他远一点。”
所以,真相究竟是什么?
我到底应该相信谁?
注:文中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我有故事
你有酒吗?
求转发
转载请注明:http://www.rongweicar.com/lyjd/50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