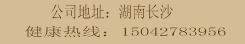![]() 当前位置: 马里 > 人口民族 > 历史学家与19世纪的日本
当前位置: 马里 > 人口民族 > 历史学家与19世纪的日本

![]() 当前位置: 马里 > 人口民族 > 历史学家与19世纪的日本
当前位置: 马里 > 人口民族 > 历史学家与19世纪的日本
《剑桥日本史(第5卷):19世纪》刚刚加印完毕,《剑桥日本史(第2卷):平安时代》和《剑桥日本史(第6卷):20世纪》的中文版不出意外也将在年年底与大家见面。下面推送的这篇文章即出自《剑桥日本史(第5卷):19世纪》的导论。深刻改变了日本的19世纪,马里乌斯·B.詹森称之为“一个终结,一个开始和一个转型”的19世纪,明治之后的日本历史学家们又将如何叙述它呢?
▲福泽谕吉
对于福泽谕吉和19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来说,问题是使日本的经验适应更大的西方历史的模式。
历史学家与19世纪的日本
马里乌斯·B.詹森
在现代日本发展的解释中,需要历史学、政治学以及价值观念的交互并用。若非如此,几乎不能对之作出正确的解释。这个从19世纪的传统中摆脱出来的国家如此急剧地从议会立宪主义转向军国主义,接着又转向和平主义,从通过战争追求国力强盛转向通过贸易追求民富国强,凡是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会追问:这到底是为什么?当代日本人距他们明治维新的祖先仅仅两代人。昭和天皇裕仁(-),现代日本的创建者明治天皇之孙,时常把战后的民主和平宪法追溯至年的《五条誓文》中所作的承诺。德川-明治时代的传统不可避免地会以当代的看法和问题意识被重新审视,而且已经被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和评估,起初是从军事成功的欢欣,最近又更多地从政治失败的创伤来加以诠释。处在历史自觉中的日本,对明治维新的理解似乎已经成为每一代人需求和希望的中心。
官方的观点,即政府领导人想要的看待事物的方式,被固定在一种忠勇行为的道德表演的模具之中。王政复古的“大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大权重归君主;一是忠诚于长期遭受忽视的天皇家族的公众情感不断深化,达于顶点。一旦天皇大权在手,他的大臣们的种种政策也就得以发展成型。天皇的诏书鼓励和表扬着他的人民和大臣。所有的成功都被归因于天皇的圣明,而由于他的仁慈,所有的困苦也都得到缓解。政府领袖们因拥有担当天皇臣仆的特权而倍感荣耀。在谈话中和讨论记录中,政府领袖们通常都会强调他们依赖于天皇的恩宠和魅力,告诫自己不得沾沾自喜。
明治政府不久就沿袭起官方编纂历史的中国传统,当然是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早在年就为此设立了一家机构,这一年年幼的天皇授权时任太政大臣的三条实美创设了史料编辑国史校正局,负责日本历史的适当保存和编纂,其意大概是想把历史编纂从幕府的偏见中解放出来,因为那些在武士世界里遭到扭曲的历史写作如今已经过时了。《复古记》(王政复古年表)就是“确立领主和臣民的功绩,显示国内文明行为及外部的野蛮行径,从而有助于王国美德的养成”指令的一个结果。这项工程的编委会集中了明治维新中央政府的主要领导,显然这些人的利益是不会被忽略的。年,天皇谕旨于文部省内设立维新史料编纂局。当该项法令被拿到帝国议会批准时,政党代表们表达了他们对一项历史工程可能具有的政治性质的担心,因为这项工程是由掌控着政府的萨摩-长州人士赞助的。作为回答,政府发言人保证政府无意书写历史,甚至连编辑文件档案也不会做。虽然如此,咨询委员会(长州的山县有朋、萨摩的大山岩和松方正义、土佐的土方久元、田中光昭和板垣退助)的性质还是表明当局是多么注意保护他们的利益。主要大名和朝廷贵族的代表出任顾问,也给这种担心提供了额外的证据。金子坚太郎男爵和长州的井上馨共同主持编纂委员会,他们亲自检查史料,并在关键点上干预明治维新过程的概述,年,十六卷本的《维新史》出版发行。
不过,在大多数方面,这些机构尚能信守它们对编纂发起者的承诺,避免进行解释性叙述。编纂局工作人员总数逐渐达到近50位专家,他们收集和检查相关文件,其中许多是家族档案集,整理成世界上最庞大的文件汇编之一。这项工程在文部省的指导下继续进行,直到年为止,一直坐落在东京帝国大学(年后改称东京大学)校园内,此后它作为史料编纂会隶属于东京大学。现在的方向掌握在东京大学历史教授会的手中,他们对文件的真实可信执行严格的标准。直到年日本投降后私人收藏向研究者开放为止,虽然接近它们要受到限制,但这些记录提供了日本19世纪中叶历史的主要来源。
直到明治时代后期为止,以一种较为普及的水平叙述和解释这些材料仍未受到重视。当整个教育系统已经建立之时,为中小学校准备教科书要求使用官方批准的日本历史版本,在这样的历史教科书中,忠诚天皇被视为美德。日本教科书的状况表明了一种以有关国家创立的史诗神话来教育日本年轻人的有意识的努力。不可避免的,政府领导人会成为这一努力的重要受益者。人们很少视同时代的人为英雄,而这正是威望层级结构在明治时代发展起来之前的状况。年,在岩仓使团和华盛顿日本使馆的年轻主管之间有着明显的分歧,迟至年,已经进入议会政府时代,驻华盛顿公使星亨仍然拒绝执行外务大臣的指示。
通过制度拔高天皇完成于年——宪法、皇室典范、教育敕语等颁布——这也就必然造成对天皇大臣们的拔高。到年带有光滑插图的一般流行杂志《太阳》创刊之时,人们已能经常看到国务大臣们身着华丽帝国服饰的照片。有位很早就担任基督教牧师的小崎弘道,他在熊本的同事曾分享过他对明治领袖们的厌恶,后来他也能带着满足感地记下,在他的集会中包括一名高官的夫人“桂公爵夫人”。
不过,到了明治晚期,19世纪60年代的斗争已经不再造成不和,而是适当地兼容并蓄。德川文化和幕府都城江户都已经成为了一种浪漫、怀旧情结的一部分。最后一任将军德川庆喜,年因奉还大政而恢复名誉,年被任命为新贵族阶级的最高等级——公爵,年以私人身份觐见天皇。王政复古的军事英雄西乡隆盛,他的功绩始于年的江户投降,终于年萨摩叛乱失败后的自杀,年也得到了天皇对他的死后赦免。这是一个充满善意的时代,某种像美国一样把内战敌对双方变得含糊不清的怀旧薄雾环绕着维新时代的人和事。
明治维新的暴力活动逐渐成为一部民族史诗,这对于创造一个有能力抵御外来威胁的国家结构是必不可少的。这部史诗的人物,无论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被纯粹的忠君概念所激活,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出错。德川庆喜的回忆录《昔梦会笔记》,记于-年间,强调了他的忠诚动机的一致性。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结构,即“国体”的创世纪神话的充分加工,实质上是20世纪明治国家晚期的产物。以一个最近研究的观点来说,“无论年前完成的是什么,更真实的是,国民心中的思想意识只是刚刚开始”。
在某种意义上,对明治晚期国民意识形态的强调被创造出来,是用以抵消一种较早前广泛流传的观点,即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使日本的经验符合于世界的经验和西方的历史,而不是强调它自己的独特性。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出版于年,论及忠君具有首要的价值,因为它能激起国民努力改进自己的国家。他争辩说:“我们应当崇敬这种天皇和我们国民联盟的国体,不是因为它倒退回日本历史的起点,而是因为它的保留将帮助我们保持现代日本的主权,并推进我们的文明。一个事物不是因其本身有价值,而是因其功能才有意义。”他又说:“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日本的政治合法性曾经时常发生变化,在这一点上它与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没有理由为此自吹自擂。”要紧的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状态,及其国民响应时代潮流的能力。这已经成为世界上每个国家历史的一个因素:“即使美国人民被击败和暂时后退,他们也会造就个伟大领袖人物(作为最初48位领导人的继承者)和10个乔治·华盛顿。”对于福泽谕吉和19世纪80年代的作家们来说,问题是使日本的经验适应更大的西方历史的模式。福泽谕吉在亨利·托马斯·巴克尔和弗朗索瓦·基佐的著作中发现了他的模型。他使用“革命”这个词汇来定义明治的变革,虽然其中包含了公众的不满作为导致幕府倾覆的一种要素,但他的观点还是更接近于经典的儒家学说,认为一次转换起因于一次时代潮流的变化,结果导致一个政府丧失了它的托管使命。福泽谕吉写道:“最终,公众舆论集中围绕着‘倒幕’这个口号,整个民族的聪明才智被指向这个单一的目标,最终结果是年的革命成功。”
随后十年,一批作者对明治维新的看法多少有了一些不同。专心致志于他们时代的民权运动,这些作者把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种种事件视为一种政治变革新阶段的预备期,把明治维新视为一个尚待完成的进程的第一步。像中江兆民这样的政治理论家满怀信心地这样言说,但对这一主题最为彻底的处理,却是由那些为大众受众写作的通才们所完成的,他们包括:德富苏峰、田口卯吉、浮田和民、山路爱山和竹越与三郎。
这些作者曾经受到麦考利和卡莱尔的思想影响,他们寻找日本的变革将会继续导致生活改善的迹象,就像紧随英国革命之后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大众民主运动的出现似乎表明,事实上日本也可以跟随西方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的道路。不幸的是,承诺依然未被履行。政治倾覆之后并未发生社会革命,而政府则依然由一个有限的地区派系所支配。这些“辉格党”的历史作家们——这是彼得·杜阿斯对他们的称呼——认为他们的任务是树立一种为“二次维新”而努力的情操,从而以一个平民社会取代他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例如,德富苏峰依据赫伯特·斯宾塞的著作,争辩日本成为一个“工业社会”的必然性,在这样的社会里,大众的情感和能力将成为建设一个强大的“太平洋上浮动码头”的基础,日本的天空将会被“成千上万烟囱升腾的烟雾所熏黑……只是因为这种可贵自由的存在,所有这些才会到来”。德富苏峰感觉到他的国家正在为此做着准备,因为物质和社会发展已经为真正有意义的进步扫清了道路。社会进步的无情规律已经导致幕府的垮台;明治维新的原因应当在对德川社会种种不满的发酵中寻找,因而明治维新的进程较少由领导人的才华来决定,更多是由于遭受压迫的人民不再忍受迫害从而产生了社会无序状态。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满含着对农村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很多人就出身于这个阶级)力量的认可,而这个阶级不断积累着对城市武士官僚的愤恨。这些“乡绅”(田舍绅士)曾是熊本社会的支配性力量,这里正是德富苏峰与浮田和民在美国内战时期的炮队长L.L.简斯的指导下度过年轻的学校生活的地方,简斯的学校曾经培养出基督教西化派的“熊本帮”。
德富苏峰、竹越与三郎、浮田和民、田口卯吉、山路爱山,及其他“辉格党”历史学家们提出了明治变革的“进步性”观点。他们认为,各种成就的取得可能是由于社会发展的推动,而不是出于领导阶层的业绩;他们对这些领导阶层仅仅表示了有限的尊重。事实上这些历史学家们怀疑,在面对公众不断高涨的政治参与要求时,领导阶层反对改革而决心保持对权力的独占,为此他们编造出自己的历史作为政治宣传。反过来,如同肯尼思·B.派尔教授对明治保守主义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对于激起一个更为保守的反对派起到了很大影响,这一派别比他们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把日本传统的价值定位得更高。关于那一激情年代的各种争议观点反映在了官方有关日本近代历史的教科书中。这是一种超越了明治变革本身的竞争,因为被渲染的绝对忠诚使得许多历史的重写成为必要,因为要选择嘉言懿行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政治上的考虑使得重新整理有关14世纪政治史成为明智的行为,从而导致帝国大学里的课程名称也被改写。
在任何与天皇朝廷有关的事物都被政治化的局面下,研究学术的历史学家们通常只能满足于离开19世纪的事件,而把它留给其他学科的学者。处于教育结构顶尖的国立大学没有近代历史的教席,学生们为毕业论文寻找议题通常也被告知,明治维新的事件距离现在仍然太近了,比较适合于政治学或新闻学。在极大程度上,这一领域被留给了像吉野作造和尾佐竹猛这样的法律史和制度史专家,他们引进了为官方机构所忽视的文集和一手出版物,经济史学家也集中北京哪能治疗白癜风北京白癜风费用大概多少
转载请注明:http://www.rongweicar.com/rdmz/187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