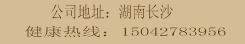![]() 当前位置: 马里 > 当地气候 > 马里亚特吉巴列霍在诗歌中永远是个追求无限
当前位置: 马里 > 当地气候 > 马里亚特吉巴列霍在诗歌中永远是个追求无限

![]() 当前位置: 马里 > 当地气候 > 马里亚特吉巴列霍在诗歌中永远是个追求无限
当前位置: 马里 > 当地气候 > 马里亚特吉巴列霍在诗歌中永远是个追求无限
“有人可能会说,巴列霍用字不加选择。他的土著风格不是故意造作出来的。巴列霍没有陷进传统和陷进历史,以便从它黑沉沉的底层去发掘失去的激情。他的诗歌和他的语言发自他的肉体和灵魂。他要表达的意思就在他自己身上。土著人的感情在他的艺术中发生着作用,而他对于这一点也许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塞萨尔·巴列霍
[秘鲁]马里亚特吉
白凤森译
马里亚特吉
塞萨尔·巴列霍的第一部诗集《黑色的使者》标志着秘鲁新诗歌的诞生。安特诺尔·奥雷戈[1]指出,“从这位播种者起,开始了一个诗歌的独立和语言发音本地化的新的自由时期”,这决不是出于友好的捧场而专大其词的评论。
巴列霍是一个家族、一个种族的诗人。在巴列霍身上,土著人的感情第一次在我国的文学中得到了纯洁的表达。作为潜在的失败的标志,梅尔加在他的“亚拉维”中还是一个古典技巧的俘虏,一个西班牙修辞学的人云亦云者。反之,巴列霍却在自己的诗歌中树立了一种新风格。土著人的感情在他的诗歌中有了自己的韵律。他的歌声完全是自己的。诗人仅仅给人们带来新的信息是不够的,他还要给人们带来新的技巧和新的语言。他的艺术不能容忍内容与形式之间那种错误的、人为的二元论。奥雷戈正确地指出,“废除陈旧的修辞结构不是诗人们的异想天开和独断专行,而是一种根本的需要。当人们开始理解巴列霍的作品时,就会开始懂得需要一种新颖的、不同的技巧”。在梅尔加身上,土著人的感情还只是在诗的深处若隐若现;而在巴列霍身上,它已是完全浮现于改变了结构的诗句之中了。在梅尔加身上它只表现为声调,而在巴列霍身上它已形成为语言。总之,它在梅尔加身上只是情爱的哀叹,而在巴列霍身上则是生活的哲学意义的体现。巴列霍是一位彻底的创新者。仅凭《黑色的使者》一部诗集,本来就足以确立他的地位。但巴列霍并不因此就没有在我国的文学进程中开创一个新时代。秘鲁诗歌(这里是就“土著人诗歌”这个意义而言),可能就是以《黑色的使者》这首诗开头的几句诗而开始的。“人生有如此沉重的打击……我不知道!那打击好似上帝的仇恨所使;在它们面前,一切不幸遭遇的苦水都好象注入了心田……我不知道!打击虽不算多,但却……凿出了条条黑沉沉的沟堑在最强悍的脸上和最结实的背上。 或许它们是野蛮的匈奴人的马驹, 抑或是死神给我们派来的黑色使者。 它们是心灵里的基督,从命运诅咒的 某种可敬的信仰上跌入深渊。 那血淋淋的打击是我们的面包 在烤箱炉口焦糊时发出的噼拍之声。 人啊……可怜的人!转回视线 就象有人从后面拍着我们的背把我们呼唤 他掉转过发狂的视线,一切往昔的经历 象罪恶的水坑倾入了眼帘。 人生中有如此沉重的打击……我不知道!”
塞萨尔·巴列霍
从世界文学的角度来分类,《黑色的使者》这部诗集,部分地(例如从它的书名来说)属于象征主义时期的作品。但象征主义是各个时代都有的东西。另一方面,象征主义比任何其他风格都能更好地表现土著人的精神。印第安人崇拜万物和喜爱农村生活,因而喜欢用拟人式的或田野的象征和形象来表达感情。此外,巴列霍只是个某种程度上的象征主义者。在他的诗歌中,如同可以找到表现主义、达达主义[2]和超现实主义一样,也可以找到象征主义的成分,特别是用上述第一种方式表现的象征主义。巴列霍的重要价值在于他是个创新者。他不断地锤炼他的技巧。在他的艺术中,表现手法总是与一种精神状态相适应。例如,当巴列霍在其创作初期借用埃雷拉—雷西格的方法时,就使它适应于自己个人的抒情心理。但他的艺术中最主要的、最典型的是印第安人的特点。巴列霍身上有一种纯正的、本质的美洲主义;但不是一种描写性的或本地主义的美洲主义。巴列霍不借用土语。他不把克丘亚语和地方土语人为地掺入他的语言;克丘亚语和地方土语在他身上是自发产生的,是他自己的细胞和肌体内的成分。有人可能会说,巴列霍用字不加选择。他的土著风格不是故意造作出来的。巴列霍没有陷进传统和陷进历史,以便从它黑沉沉的底层去发掘失去的激情。他的诗歌和他的语言发自他的肉体和灵魂。他要表达的意思就在他自己身上。土著人的感情在他的艺术中发生着作用,而他对于这一点也许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认为,巴列霍的土著主义最显著、最明确的特征之一,是他经常表现出的怀旧情感。巴尔卡塞尔[3]——也许我们应该感谢他,是他最准确地表现了土著人的心灵——说,印第安人的悲伤就是对过去的眷恋。而巴列霍就是个纯粹的怀旧者。巴列霍具有忆念过去的感染力,但他的怀旧总是主观性的。不应该把他那用如此抒情的纯洁性构思而成的怀旧情绪,与复古主义者的文学怀旧情绪混为一谈。巴列霍是怀旧的,但不是单纯地向后看。他不象佩里乔利式的复古主义怀念总督辖区那样怀念印加帝国,他的怀旧是一种伤感性的抗议或心理的抗议,是流亡异地的怀旧情绪,是离乡背井的怀旧情绪。
塞萨尔·巴列霍
“我的象水仙花和灯笼果一样的安第斯山的温柔的丽塔 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 须知毕桑西奥[4]使我感到窒息 血液象蹩脚的白兰地在我体内昏昏欲睡。” (《黑色的使者》:《死去的牧歌》)“兄弟,今天我坐在屋前的石凳上 多么渴望你能坐在我们身旁 回想起此时此刻我们曾一同玩耍 妈妈抚摸着我们说:‘哎哟,这些孩子……’” (《黑色的使者》:《致我的兄弟米格尔》)“今天我独自一人用午饭,没有母亲,没有人劝我多加餐, 没有人为我拿水喝,也没有人说:‘你吃呀’, 没有父亲,往日在喃喃细语的圣餐时 每当他姗姗来迟 他总是扯开话题询问为何这般沉寂。” (《特里尔塞》:第二十八节)“陌生人已经死去,你曾和他 深夜而归,没完没了地交谈。 再也没有人把我等盼 布置好我的住所,把乱糟糟的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 炎热的下午已经过去, 你伟大的港湾,你的咆哮; 和你那死去的妈妈的闲谈, 往昔,下午她总给我们端来满满的一杯茶。” (《特里尔塞》:第三十四节)在另外一些时侯,巴列霍预感或预言了即将来临的怀旧情绪。“人已不在!那天早晨, 我象悲伤的小鸟, 飞向那无声的帝国和阴森之海的海滩, 那白色的公墓就是你的栖身地点。”(《黑色的使者》:《人已不在》)
“夏天,我就要走了。你那黄昏时柔顺的纤手使我悲伤;
你虔诚而至,来不逢时, 在我的心灵中你将找不到任何人。” (《黑色的使者》:《夏天》)
巴列霍是在他的所有怀旧之感,由于受到三个世纪的痛苦的刺激而变得愈加强烈的时刻,表现这个种族的。但是——而且在这一点上可以辨认出印第安人灵魂的一个特点,巴列霍的回忆充满了他所喜欢的那种嫩玉米的香甜味道,正如他在向我们谈到“奉献嫩玉米的圣餐仪式上那没完没了的祷告”那样。巴列霍的诗歌中有印第安人的那种悲观主义情绪。他的踌躇,他的疑问以及他的不安,都被以怀疑态度化成了一个“干嘛呢。”在这种悲观主义情绪中,总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内容。在这种悲观主义情绪中,没有一丝一毫邪恶和病态的东西。这是一种如皮埃尔·昂普所说的,忍受和赎回“人的痛苦”的灵魂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主义情绪的产生没有任何文学的渊源。它没有表现出被莱奥帕尔迪[5]或叔本华[6]的声音所干扰的少年人的浪漫式的绝望。它总结了富有哲理性的经验,概括了作为一个种族和一国人民的精神态度。不要到它那里去寻找与西方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或怀疑主义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相近之处的东西。如同印第安人的悲观主义一祥,巴列霍的悲观主义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感情。它与东方的宿命论有一种模糊的联系,这使它更加接近于奴隶们的基督教或神秘教的悲观主义。但它与导致安德烈耶夫[7]和阿尔季巴切夫笔下精神错乱者的自杀的那种痛苦的伤感没有共通之处。可以说,它既不是一种概念,也不是一种神经官能症。
塞萨尔·巴列霍
这种悲观主义充满了柔情和仁爱。这是因为它不是令人失望的、强烈的自我崇拜和孤芳自赏孕育而成的,就象浪漫主义时期几乎所有的情况那样,巴列霍感受着人间的一切痛苦。他的痛苦不是个人的痛苦。对于人们的悲伤,甚至上帝的悲伤,他的心灵“至死也感到悲痛”,因为诗人认为,不仅存在着人们的痛苦。他在下面的诗句中向我们谈到了上帝的痛苦:“我感到上帝与下午和大海 在我的心底漫步。 我们与他同去。天色渐黑。 无靠无依……我们与他一起迎接夜幕降临。 但我听到上帝的脚步。甚至他好象 在向我指明我也说不清的一种美丽的色彩。 他象一位殷勤的主人,善良又悲哀; 恋人那甜蜜的睥睨已失去生气: 他的心应感到痛苦万分。 啊,我的上帝,我刚刚来到你身旁, 今天下午我爱得如此强烈: 因为在胸脯这个虚假的天秤上 我凝视着一个脆弱的造物,并为之哭泣洒泪。 你,哭得如此伤心…… 你对如此丰满的胸脯一往深情…… 我把你奉为上帝,因为你爱得如此之深; 因为你从不微笑,因为 你的心可能经常痛苦万分。”巴列霍在其他诗篇里否定了对上天的这种直观感觉。在《永恒的欺诈》中,诗人怀着怨恨的苦痛对上帝这样说道:“你倒一向安乐自在,对你的造物不予一点关怀。”但一向由同情和爱所构成的诗人的真实感情却不是这样。当他的抒情风格完全摆脱理性的强制时,他的诗情就会舒展而丰富地流泻出来,表现为如下的诗句,就是这些诗句十年前最早向我展现出巴列霍的天才:“卖彩票的人高声喊道:‘一张彩票可得奖一千元’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上帝心肠。 多少张嘴在向他要求, 他已经感到意乱心烦, 咧开嘴唇说了声不卖。 难道卖彩票的人 象上帝一样徒有其名, 在为人们聚积着无望的仁爱。 我望着那人一身破衣烂衫, 他本可以把心给我们献上, 但他高声叫卖的手里那张彩票, 却象一只无情的飞鸟 不知飞到何处栖身。这一点, 那流浪汉上帝 既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就是这个温煦的星期五, 他身负行囊,沐浴着阳光。 我要问: 上帝为什么决意打扮成彩票商?”奥雷戈写道,“就这位诗人本人来说,他使自己的语言具有个性化的特点,但就他思考问题、表达自己的感受和爱来说,他是从宇宙的角度出发的”。这位伟大的抒情诗人,这位伟大的主观诗人,他的表现象是宇宙和人类的解释者。他的诗中没有任何使人想起浪漫主义那种自我崇拜和孤芳自赏的哀怨的东西。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实质上是个人主义的,相反二十世纪的浪漫主义却自然地、必然地是社会主义的和一致主义的。从这个观点来说,巴列霍不仅属于他那个种族,而且也属于他那个世纪和他那个时代。
塞萨尔·巴列霍诗选
他的人道同情心如此强烈,以致于他有时感到对人们的一部分痛苦负有责任。于是他引身自责。他会为自己好象也在偷窃别人而突然产生一种恐惧和坐立不安:“我全身的骨骼都属于他人. 或许是我偷来之物! 我生来所具有的这些东西, 或许本应赋予他人; 我想假如我没有出生 另一个可怜人会来喝这杯咖啡! 我往何处去?……我这个可恶的窃贼! 在这寒冷的时刻,大地散发着 人的埃尘,显得如此悲哀, 我多么想把所有的房门敲击, 不知向谁哀求饶恕, 多么想为他烤制一块块新鲜的面包 就在这里,在我心中的火炉……!”《黑色的使者》这首诗总是这样。巴列霍的心灵完全献给了穷人的苦难。“赶马的人啊,你汗流如注把路赶。 梅诺库乔庄园 为了生活每日都有千种忧烦。”这种艺术标志着一种新的艺术感的诞生。这是一种新的艺术,一种具有叛逆性的艺术,它打破了宫廷丑角和帮闲文人的文学那种宫廷传统。这种语言是诗人和人的语言。《黑色的使者》和《特里尔塞》的杰出作者,这位从集市上流浪艺人所极力赞美的利马街头走过时,无人注目和知晓的伟大诗人,在他的艺术中,是作为这种新精神和新觉悟的先驱而出现的。巴列霍在自己的诗歌中永远是个追求无限、渴望真理的人。同时,在他身上,创作的痛苦和欢乐也是难以描述的。这位艺术家只希望纯洁无瑕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因此,他不要任何词藻的雕琢,他摈弃了任何文学上的浮夸。他在形式上达到了最冼炼、最朴实和最引以自豪的简洁的程度。他是一个刻意追求语言简朴的人,他脱掉鞋子,让自己光赤的双脚去领略他的道路多么崎岖,多么艰难。在他发表《特里尔塞》之后,他给安特诺尔·奥雷戈写了这样一封信:“这部诗集是在极度空虚中产生的。我对他负责。我对它的美学观点承担全部责任。今天,也许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感到,我肩负着一项作为人和艺术家前所未有的、最神圣的义务,即自由行动的职责。如果我今天不能自由,我将永远不会自由。我感到,这项义务那股最有权威的雄赳赳的力量,给我弓形的前额平添了许多条皱纹。我已找到我所能找到的最自由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我艺术上的最大收获。上帝知道我的自由多么真实和实在!上帝知道,为了使节拍不致超越这种自由而流于放荡,我经受了多少折磨!上帝知道,为了使我那可怜的灵魂活下去,我曾胆战心惊地走到了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崖边,但又担心一切都断送在崖底!”这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创新家、一个道地的艺术家的特点。他这篇对自己的苦难的自白是他的伟大之处的最好证明。
(出自马里亚特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之《对文学的审理》第十四节)
译注:[1]安特诺尔·奥雷戈(—),秘鲁诗人、杂文作家。[2]达达主义是始于年的先锋派艺术运动,主张取消思维与表现之间的一切联系。[3]路易斯·爱德华多·巴尔卡塞尔(—)秘鲁史学家、作家。对秘鲁印第安人历史颇有研究,著述甚多。[4]毕桑西奥:伊斯坦布尔城古名。[5]贾科莫·莱奥帕尔迪(—),意大利浪漫派诗人,著有《歌集》等。[6]叔本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7]列昂尼德·尼古拉耶维奇·安德烈耶夫(—),俄国小说家、剧作者。年因贫困自杀获救,思想反共,移居芬兰至死,作品充满悲观气氛,著有《七个上吊的人》。
推荐阅读
迪诺·布扎蒂:弄假成真的死者
马里奥·贝内德蒂:仿佛子弹打进一堆烂草里
马里亚特吉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年),秘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作家,拉丁美洲杰出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青年时期旅居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年回国后积极参加反对A.B.莱吉亚独裁统治的斗争。年他创建秘鲁社会党,后改称秘鲁共产党。同年12月出版《阐述秘鲁现状的七篇论文》,该书被视为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作品,核心思想是解决印第安人和土地问题,反对拉丁美洲大庄园封建制。年发表著作《捍卫马克思主义》。近期精彩推荐
导读人:
敬文东
胡传吉
谢宗玉
李约热
李德南
乔叶
鲁敏
娜夜
莫非
荆永鸣
芬雷
慕容雪村
贾冬阳
西渡
泉子
朱白
黄惊涛
蓝蓝
哑石
李宏伟
申霞艳
蒋浩
何平
朱庆和
金特
陈先发
连晗生
苏画天
陈梦雅
庞培
陈律
蔡东
赵四
作家:
阿莱霍·卡彭铁尔
博尔赫斯
R·S·托马斯
彼得·S·毕格
德米特里·贝科夫
谢默斯·希尼
苏珊·桑塔格
帕斯捷尔纳克
南希·克雷斯
乔治·佩雷克
T.S.艾略特
毛姆
叶芝
马斯特斯
塞林格
理查德·耶茨
奥登
皮兰德娄
J.希利斯·米勒
米洛拉德·帕维奇
霍夫曼斯塔尔
本雅明
莱辛
庞德
田中芳树
沃尔科特
埃德蒙·雅贝斯
赫拉巴尔
萨瓦托
赫尔曼·黑塞
赫塔·米勒
胡安·鲁尔福
艾萨克·辛格
雷蒙德·卡佛
勒克莱齐奥
马尔克斯
奥康纳
穆齐尔
梅里美
埃利亚斯·卡内蒂
克莱尔·吉根
E.B.怀特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屠格涅夫
大卫·华莱士
当代写作者:
黄惊涛
金特
黎幺
东荡子
陈梦雅
毕飞宇
李宏伟
孙智正
万夏
魔头贝贝
彭剑斌
马松
司屠
陈集益
冉正万
甫跃辉
茱萸
马拉
朱琺
大头马
王威廉
朵渔
李约热
王小王
冷霜
贺奕
胡桑
凌越
须弥
何小竹
冯冬
雷平阳
刘立杆
西渡
蓝蓝
赵松
曹寇
颜歌
朱庆和
李静
张光昕
顾前
杜绿绿
文珍
魏微
庞培
赵野
陈东东
郑小驴
叶弥
江汀
吴玄
陈律
桑克
郭爽
选稿:杜绿绿
本期编辑:张晓敏
欢迎转发、分享,其他公号如需转载,请与“未来文学”订阅号后台联系。
马里亚特吉赞赏
转载请注明:http://www.rongweicar.com/ddqh/297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