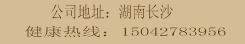布考斯基
▼
查尔斯?布考斯基(CharlesBukowski,-),美国洛杉矶人氏,诗人、作家兼酒鬼,二十世纪垮掉派乃至整个世界文学界最牛逼的“脏老头”(DirtyOldMan)。《时代》杂志称之为“美国底层的桂冠诗人”,其生活作派、吃苦受罪、嗜酒如命的态度以及与女人的关系等均成为美国穷人日常生活的 写照。
布考斯基一生主要以洛杉矶为写作大本营,嗜好喝酒、泡妞及赌马,笔下人物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以下三滥居多。他早年曾尝试打入文坛,零星地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后希望彻底破灭,便专心致志做起酒鬼,自称要将所有才华挥霍到酒盅上。他周游美国各地,以打零工度日,干的多是薪酬微薄的苦力活,如装卸工、清洁工等。每份工作皆干不长,几个月或是几星期,有些甚至只干了一天便掉头走人。如此生活了十年,穷困潦倒,丢人现眼,一度接近 边缘。最终在一次酗酒吐血几乎挂掉之后,才被迫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邮局工作。日后他根据这段经历写了《邮局》(PostOffice)和《样样干》(Factotum)等多部小说。
布考斯基出生于德国,其父为美国大兵,其母为德国人,二人结识于一战结束后的德国。三岁那年,全家搬回美国,最终在洛杉矶落脚。布考斯基自幼孤僻,不善交际,后因痤疮问题而更加自闭。据说,邻居小孩时常取笑其德语口音以及父母给他穿的衣裳。高中毕业后他就读于洛杉矶城市学院,学期两年,专修文学与艺术。讽刺的是,这段学院经历对他日后找工作的帮助微乎其微,有时甚至要故意隐瞒学历,谎称高中毕业。
布考斯基自称被父亲的拳头揍大,曾写过长篇小说《黑面包火腿》(HamonRye),记叙自己成为另类硬汉的经历。在父母眼中他是个怪胎,胸无大志,吊儿郎当,整天喝酒打架瞎逼混,偶尔还出入班房。与父母关系的冷漠或许加深了他对人情世故的厌倦,厌倦舞会,厌倦派对,厌倦人群,厌倦爱情,厌倦一切正常人孜孜以求的美好快乐。“我是个靠孤独过活的人,孤独之于我就像食物跟水。一天不独处,我就会变得虚弱。我不以孤独为荣,但以此维生。”布考斯基的这段表白与张楚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所传达出来的那种反讽很有些异曲同工之妙。
老头的诗歌平淡如大白话,多为生活哲学及日常琐事,出版过的诗集包括《鲜花、拳头及嚎啕大哭》(Flower,Fist,andBestialWail)《水烧火淹》(BurninginWater,DrowninginFlame)《爱为地狱之犬》(LoveisaDogfromHell)《弹醉琴/如击鼓/直到手指滴血》(PlaythePianoDrunk/LikeaPercussionInstrument/UntiltheFingersBegintoBleedaBit)等数十部。为谋生,他曾给《好色客》和《花花公子》等 色情杂志撰写过诸多脏乱差的黄色小故事,读来令人头晕目眩、眼花缭乱,感兴趣者可以移步网络去围观。
折腾了大半辈子之后,年,布考斯基终以73岁高龄死在南加州小镇圣佩德罗(SanPedro),墓志铭为“DontTry”。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曾如此阐释:“不要尝试,既不要为了凯迪拉克而尝试,也不要为了创作或为了不朽而尝试。你要等,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就再等。就好比墙上有个虫子,你要等它向你爬过来。等它爬到足够近的地方你再出手,拍下来打死。或者你喜欢它的样子,那就把它当成宠物来养。”
布考斯基对美国文化影响甚远,有多部小说被改编为电影,包括《苍蝇酒吧》(Barfly)和《勤杂多面手》(Factotum)等。其大牌粉丝包括好莱坞 西恩?潘、马特?狄龙、米基?洛克等,歌手里则有莱昂那多?科恩跟汤姆?维茨这样的超级魅力老男人。尤其是汤姆?维茨,同样混在洛杉矶,无论唱歌打扮都深受偶像的影响,歌曲也多有《世界的底层》(BottomoftheWorld)这样类似的主题。此外,U2主唱波诺也曾向其致敬,却被他无情地抨击为“百万富翁摇滚大明星,无论如何都是他自己所反对的体制的一部分”。老头的个色可见一斑。
文章节选自《样样干》中文版前言马里万
《样样干》选读
▼
我在一间屋子里醒来。醒来发现只有一人。天刚蒙蒙亮,依然有点冷,我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衣。我在想这是怎么回事。我从硬床板上爬起来,走到窗前。窗户上装有铁栏杆,外面则是太平洋。(不知怎么搞的,我竟然是在马里布海滩。)过了个把小时,看守走过来,铁碗跟托盘叮当作响。他把早餐递给我。我坐下来,一边吃饭一边听着外面的海浪声。
又过了四十五分钟,我被带到外面。有一排人被一根长链栓在一起。我走到队伍后头,主动伸出两手。看守说,“没你的事。”我被单独戴上一副手铐。两个警官把我塞进警车,驾车离去。
到了卡尔弗市区,车停在法院后面。其中一个警察带着我下了车。我们从后门走进法院,坐在审判室的前排,他给我打开手铐。我一直没见到提米。法官一般都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过来。我的案子是第二桩。
“你被指控在公共场合醉酒闹事外加妨碍交通,监禁十天或罚款三十美元。”
我认罪,尽管搞不懂自己什么时候妨碍交通了。警察把我带到楼下,塞进警车后座。“你小子够幸运的,”他说,“你们两人搞得交通堵塞,算是英格坞有史以来堵车最厉害的一次。”
随后他把我拉到洛杉矶县看守所。
当天晚上,父亲带着那三十块钱罚金过来了。刚出看守所大门,他便泪眼汪汪。“你真给你妈跟我丢人,”他说。他们好像认识其中一个警察,那警察还问他,“支那斯基先生,你家大少爷怎么进来了?”
“我都快丢死人了,自己儿子蹲看守所。”
我们走进他的车里,他驾车离开。路上他还在哭。“现在是二战,你竟然不肯参军打仗,报效祖国……”
“精神科医生说我不合格。”
“我儿啊,要不是参加一战,我怎么也不会遇到你妈,也就不会生下你。”
“有烟吗?”
“现在你倒进了监狱。这种事还不把你妈给气死。”
路过下百老汇街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廉价酒吧。
“进去喝一杯吧。”
“什么?你喝酒都喝到牢里去了,这刚放出来,又想喝?”
“这会儿是最需要喝两口的时候。”
“千万别跟你妈说你刚出牢门就想喝酒。”他警告我。
“我还想泡个小妞。”
“什么?”
“我说,我还想泡妞。”
他差点闯了红灯。接下来我们没再说话。
“顺便告诉你,”他 说道,“我猜你也知道,这笔罚款
会记在你的食宿费上,知道吧?”
我在鲜花大街的一家汽车配件厂找到了工作。经理又高又丑,屁股很小。只要他头天晚上跟老婆干过,第二天总要向我汇报。
“昨晚我干了我老婆。先把威廉兄弟的订单拿过来。”
“K-3号轮缘缺货。”
“通知他们缺货。”
我在包箱跟发货单上戳上“缺货”二字。
“昨晚我干了我老婆。”
我把威廉兄弟的箱子用胶带粘上,贴上标签,称重,贴上邮票。
“干得好爽。”
他留着沙黄色的小胡子,沙黄色的头发,屁股上没长肉。
“ 她射了。”
……
我那辆三十五块钱买来的破车还在。赌马很热门,我们很热衷。简跟我对赌马一无所知,但是运气极旺。那会儿赛马比赛分八场,而非九场。我们有一招诀窍——叫做“哈尔马兹第八场”。威利·哈尔马兹胜出普通赛马师一大截,但是他有体重问题,像现在的霍华德·格兰特一样。在研究过胜负表之后我们发现,哈尔马兹通常会在 一轮比赛中胜出,赔率通常都很高。
我们并非每天都去赌马。有些早晨喝得太醉了病在床上起不来,要到午后才起床,然后去烟酒店光顾一趟,再去酒吧里打发个把钟头,听听点唱机,看看酒鬼们,抽烟,干笑——真是打发时间的好方式。
我们真够幸运的,每次赶到赛马场都恰逢吉日。“现在你看,”我会告诉简,“这回他不会再输了……不可能的。”
紧接着威利·哈尔马兹就出现了,跟过去一样冲刺终点,冲破黑暗跟酒水,脱颖而出——善良的老威利带来了16:1、8:1、9:1的赔率。当全世界都变得冷漠弃我们而去时,只有威利一直在拯救我们。
那辆三十五块钱的破车几乎每次都能启动,这没问题;问题是车头灯不肯亮,而每次赌马在第八场结束后天就黑了下来。简通常会带一瓶波尔图葡萄酒放在钱包里。我们会在看台上喝啤酒——若赌马顺利的话就转到赛马场的酒吧里去喝,通常都是威士忌兑水。我已经有过一次醉驾记录,现在又开着一辆车头灯不亮的破车,基本上弄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
“别担心,宝贝,”我会说,“再颠一次车灯就能亮了。”咱们有减震失效的优势。
“这儿有个斜坡!抓住你的帽子!”
“我没戴帽子!”
我会把油门踩到底。
砰!砰!砰!
简被颠得七上八下,但仍不忘抱紧那瓶波尔图葡萄酒。我会牢牢握住方向盘,瞅准前面路上的零星亮光。每次这么颠簸都能把车头灯颠亮,有时迟有时快,但总能把它颠亮。
我们住在一栋老房子的四楼,楼背面的两间屋。房子坐落在悬崖峭壁上,从后窗往外看,好像有十二层楼那么高,不止是四层。很大程度上也像是住在世界的边缘——世界崩溃之前的 一处避难所。
此时,我们在赛马场上的一连串好运终结了,所有的好运都终结了。钱只剩下一点,而我们还在酗酒。波尔图跟麝香葡萄酒。我们在厨房的地上摆满了六七个装满烈酒的加仑壶,加仑壶前面摆着四五瓶威士忌,威士忌前面又摆了三四瓶酒。
“总有一天,”我告诉简,“等世界被证明是四维的而不是三维的,人就能够随便出去散散步然后永无踪迹地消失。没有葬礼、没有眼泪、没有幻想、没有 也没有地狱。人们可以随便坐着问上一句,‘乔治去哪儿了?’有人回答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刚才他说他出去买包烟。’”
“听着,”简说,“现在几点了?我想知道几点了。”
“好吧,让我看看,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我们按照收音机里的时间对过一次。这钟每小时多走三十五分钟,现在显示的是晚上七点半,但很明显不对,天现在还没黑。算算看,七个半小时过去了。七乘以三十五分钟,是两百四十五分钟,半小时乘以三十五等于十七又二分之一分钟,总共是两百五十二又二分之一分钟。好了,总共快了四小时四十二又二分之一分钟,我们把时间调到5:47。现在是5:47,是晚饭时间,我们却什么吃得也没有。”
我们的钟被摔坏了,我修过几次。我把后盖卸掉,发现主要的发条跟飞轮坏了。为了让时钟转起来, 的办法就是把主发条缩短收紧。这样一来便影响了指针转动的速度,几乎能看见分针在移动。
“再开一壶酒,”简说道。除了喝酒做爱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什么可干的了。
我们吃光了所有能吃的东西。晚上会出去散步,到别人的汽车仪表盘跟车前柜里偷香烟。
“要不要再做一块煎饼吃?”简问道。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塞下一块。”
黄油跟猪油都吃完了,简烙起了干煎饼。烙出来的不再是饼子——面粉掺水而已。吃起来很脆,非常脆。
……
我在汽车配件行干的活越来越少。老板曼茨先生走过来时,我不是蹲在角落里就是过道里,极为懒散地把货物往货架上搁。
“支那斯基,你没事吧?”
“没事。”
“没生病吧?”
“没有。”
曼茨先生随后走开。这种事重复了一遍又一遍,很少变化。有一次他逮到我在货物清单后面画小巷的素描。我的口袋里装满了赌金。宿醉还不算太坏,只有花钱买 的威士忌才能喝成这样。
我又领了两个多星期的薪水。随后在某个星期三早上,曼茨先生站在办公室附近的走道中间,招手示意我过去。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曼茨早已坐在办公桌后面。“坐吧,支那斯基。”桌子中央放着一份工资单,正面朝下。我将工资单正面朝下划过玻璃,看也不看便塞进钱包。
“知道我要让你走人了吧?”
“老板的心思从来都不难揣测。”
“支那斯基,你这个月压根就没好好干活,你自己清楚。”
“再怎么累死累活你也不会赏识的。”
“支那斯基,你根本就没有累死累活。”
我盯着鞋子打量了一阵,不知道说什么是好。随后我看着他。“我把时间都给你了。我总共就那么多时间——任何人也就那点时间。就为了一小时能挣那一块两毛五分钱。”
“记住你当初可是求着我要干这活的,你说工作就是你第二个家。”
“……我干了多少活你才能住在山上的大房子里并且拥有一切配套的东西。如果说有人在这笔买卖或者说这种安排上有所损失……我才是赔了,明白不?”
“好吧,支那斯基。”
“好吧?”
“是的,你走吧。”
我站起来。曼茨身穿一件传统的褐色西装,白衬衫,大红色的领结。我想给这结局来个神来之笔。“曼茨先生,我想拿到我的失业保险,这事我不想有任何麻烦。你们这种人总是剥夺工人的合法权益,所以不要给我制造任何麻烦,否则我回来找你算账。”
“你会拿到失业保险的,现在赶紧给我滚!”
我从那里滚了。
手上攥着赢钱跟赌金,又整天呆在家里,简很喜欢我这样。两星期后我开始领失业津贴,心态无比轻松,成天做爱跟流连酒吧。我每周去一趟加州就业局,排队,领津贴。每次只要回答三个问题就行了:
“你能工作吗?”
“你想工作吗?”
“你愿意接受工作吗?”
“是!是!是!”永远都是肯定答案。
我还要上交一份上周去面试过的三家公司的名单。这些公司的名称跟地址都是我从电话本里翻出来的。每次有申请人对上述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说“不”时我总是很惊讶。他们的失业津贴会立刻被扣留,紧接着被带进另外一个房间。在那里,经过特殊培训的专业顾问将把他们打发回贫民窟。
不过就算有失业补助跟赌马赚来的存款,我的钱很快还是挥霍一空了。简跟我一旦喝高了就变得无法无天,麻烦层出不穷。我总是跑到林肯高地监狱去把简保释出来。她每次都是被同性恋女狱警拽着胳膊乘电梯下来,每次不是黑眼圈就是破嘴皮,经常身上还有虱子,被酒吧里遇到的某些疯子给传染了。然后是缴纳保释金、出庭费用跟罚款,外加被法官要求去参加六个月的A.A.会议。我也经常会被缓刑处理并上缴大笔罚金。简试图将我从强奸未遂、恶意攻击、暴露下体、当众猥亵等恶行带来的大笔罚金中解脱出来,但扰乱社会是我的一大嗜好。大部分指控并不会把我带进监狱服刑——只要缴了罚金。但这可真是一笔巨大的持续花费。我记得有天晚上我们那辆破车刚好在 公园门口抛锚了。我盯着后视镜说道,“好了,简,算咱们走运,有人能推咱们一把了,他正从后面赶上来。丑恶世界还是有那么个把好人的。”然后我又看了一眼:“坐紧了,简,他要来撞我们了!”那个狗日的不带减速直接就撞了上来,撞得如此之狠,前座都塌了下来,我们被摔了个四仰八叉。我从车里爬出来,质问那家伙有没有在中国学过开车。我还威胁要杀了他。警察赶了过来,问我是否介意吹他们的小气球。“不要吹,”简说。我没有听她的。不知怎的,我当时想的是,既然那家伙开车撞我在先,我就不可能被判醉酒驾车。我记得 是我进了警车,留下简独自站在那辆前座崩塌的破车旁边。类似的事故接踵而至,破了大把大把的钱财。我们的生活一点一点地走向崩溃了。
联邦走马出品▼
《脏老头手记》
《样样干》
以上两本书均已售罄,请期待《低俗:为了一种坏写作》,将由联邦走马制作。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rongweicar.com/lsyg/7480.html